
丛林蹲守——搜索美制高空无人侦察机飞行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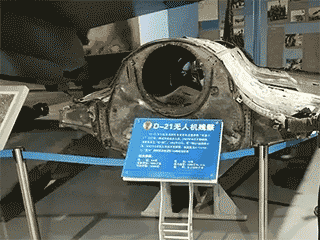
中国军事博物馆兵器陈列大厅的一角,立着一架美制高空无人侦察机,旁边的说明牌上记载,美制高空无人侦察机,1971年3月坠落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原始森林里。看到这段记载,一段往事清晰地在脑际浮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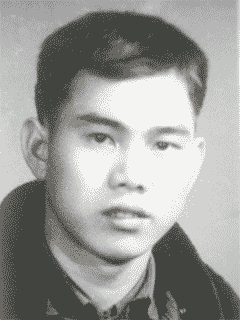
半个世纪前的1971年,我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四营营直属通讯班供职,又是营部执勤小分队队员。3月6日上午,我从通讯器材库推出“五一”牌载重自行车,将装有文件的挎包斜背在肩上,来到营长(刘慎山)、教导员(荀瘖把)的办公室,喊了一声:“报告,营长教导员,我要去十一连送文件,午饭由炊事班送来(营部指定我负责营长,教导员的生活起居,日常由我去炊事班将营长,教导员的饮食取来)”。我话还未说完就被教导员挥手制止:“将文件退回机要科,由他们派人去送,你哪儿也别去,等会要参加一个会议。”我答应“是”,敬礼,转身离去。

九时,营部会议室里坐着营长,教导员,副营长邓绍辉,营党委机要秘书刘福元,机要科科长刘继贤,保卫科科长雷松柏,机务排副排长江丛发和驾驶员伍解放,离营部较近的一连连长和二连副连长;营部炊事班班长杜忠思,还有我,计十二人。教导员主持会议,营长简明扼要地说了会议的内容:“昨天,境外蒋残匪的两架飞机飞临思茅地区上空侦察,被击落一架,另一架受伤,飞行员抛弃副油箱后跳伞,估计降落在我师所辖境内,师部命令各团在飞行员可能出现的区域,安排人力进行搜索,同时在地势较高的地方设置固定观察哨直到抓获飞行员为止。营长接着说:全营十一个连队,都要设立固定观察哨和组织搜索队。三连至十一连由保卫科把会议内容通知下去,最迟明天下午进入情况;营部设固定观察哨的地点和人员安排由邓副营长负责。我、教导员、刘秘书马上要去团部开会,没说到的请教导员补充。教导员:我想说的就是这次搜索行动,最好以野外训练为名而且要保守秘密,除我们三人要去团部开会外,在座的都应去参加,人员不够,可以多安排几个组织纪律性强的,各连除设固定观察哨外,搜索队员还要能吃苦耐劳,要当做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

营长、教导员、刘秘书以及一连连长、二连副连长,离开会议室后,邓副营长要通讯班叫来组织科尹科长和机要科刘科长、保卫科雷科长、机务排江副排长,驾驶员伍解放、炊事班长杜忠思和我留下来继续开会。因尹科长前面未到会,邓副营长将营长、教导员的话复述了一遍,接着大家商议,认为:营部的观察哨只能设在拿巴山,那里地势高,离营部直线距离很近,便于随时与营部保持联系。邓副营长安排保卫科雷科长准备枪支弹药,与会八人人手一支;炊事班杜班长另从炊事班带上两人,准备十人大约半个月的伙食;洗漱用品和行李自备;江副排长和伍解放同志先行一步,下午就出发去拿巴山下的曼拿巴寨找到生产队长和民兵队长,请他们予以配合;会后我立即与勐养公社党委电话联系,请他们与曼拿巴寨沟通;明天早晨七点在营部汇合。

三月七日早上七时,机务排的周章生已开来一辆“东方红”40型拖拉机,大家将物品搬上车,邓副营长肩上还挎着一支双筒猎枪。拖拉机开到离营部四公里的四连,连长已在等候,我们搬下物品,在四连用完早点,背上物品,扛着“半自动”,徒步进入山林。为何不从营部前往曼拿巴寨而要绕道四连上山?大家当时很疑惑,邓副营长事后解释:一则营部东面的河流冲刷,山体很是陡峭,背着物品攀援,极不安全,稍不留神,就会造成人员伤亡,物资损失;二则中缅边境虽无战事,但敌特亡我之心不死,时不时会潜越边境制造事端。我们荷枪实弹,目标太大,且容易泄露行藏,不利隐蔽。

进入林间小路,山势相对比较平缓,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路,只能说曾经有人或者动物经过。越往森林里走,越是艰难,藤蔓缠绕,荆棘挡道,好在炊事班带了一把短柄砍柴刀,一边走,一边砍掉那些扯衣拖脚的荆棘藤条,行进速度慢如蜗牛;进到深处,见不到阳光,分不清方向,只觉得昏暗一片。邓副营长一看手表,已是下午时分。大家不由的埋怨江副排长:怎么不留下记号?邓副营长吩咐炊事班准备午餐,大家啃着馒头,就着咸菜,喝几口冷水,哄着肚子又出发了,好几次走了回头路。直到听到不是布谷鸟的“布谷鸟”叫声,大家松了一口气,那是江副排长和伍解放的联络信号。其实不是江副排长不留记号,而是我们走岔了路。下午四时,终于到达曼拿巴寨的“公房”,所谓“公房”实际就是傣族“卜冒”“卜少”(少男、少女)谈情说爱的地方,如今暂时成了我们的“行营”。

生产队长岩包依和民兵队长岩依坎正带领民兵在修检“公房”;有的上房加盖棕叶,有的打竹笆修理竹笆墙,还有的打扫卫生,有几个年龄五十上下的“波涛”在制作连排竹床。见我们到来大伙儿一边忙着一边点头微笑,以示招呼。太阳吻着山林林梢时,住处基本收拾妥当。邓副营长和江副排长(会说傣语)正和岩包依,岩依坎说着什么,江副排长当翻译,过了一会儿,岩包依和岩依坎领着几个“波涛”和民兵走了,杜班长和两个炊事员埋锅造饭,我们则在竹笆床上摊开了铺盖。

“公房”离寨子一公里左右,紧邻水流平缓的拿巴河,“公房”不远处,一条小溪从拿巴山蜿蜒而下,在离河岸二十米处形成一个浅潭后注入拿巴河。浅潭中一大截两人合抱粗的枯木一半露出水面,在水潭周边的花草映衬下,别有一番韵味。夜色降临,看不清河水,溪水的颜色,隐约中只觉风轻树静,山野寂寂,倦鸟归林,一切仿佛静止。其实这只是前奏,夜,永远属于那些精灵们;夜,是另类生灵们的舞台……

晚饭后,杜班长和两个炊事员在简易“厨房”收拾炊具,我们则躺在床上听邓副营长安排工作:会讲傣语的江副排长和尹科长,刘科长去寨子走动走动,了解一些情况;雷科长检查枪支,配置弹药;我和伍解放与民兵们一起,上山寻找搭建观察哨棚的大树;炊事班的三人,加固简易厨房,能防雨挡风;待树上观察哨棚搭建好后,我和伍解放为一组,雷科长和尹科长为一组,刘科长和江副排长为一组,邓副营长和杜班长为机动,日夜轮值,看见烟火就鸣枪告警,民兵和未值守的人员则进行围堵抓捕。邓副营长的话一说完,房内则传出了轻微的鼾声……

第二天(也就是国际“三八妇女节”),按往例,兵团的妇女会放假一天,但今天情况有变,全部上岗。刚吃好早饭,四个相当年轻的“比崽”(已经结婚的傣族男子)就已经站在我们面前,用非常生硬且极不顺畅的汉语笑呵呵地连比带划地告诉我们:是队长岩包依叫他们过来寻找大树,建盖观察哨棚的。邓副营长和他们一一握手,连声感谢。听到江副排长的“翻译”,他们笑得更欢了——这么大的官跟他们握手,多荣耀啊!能不开心么?江副排长用傣话介绍我和伍解放跟他们一起去,他们四个伸出大拇指一齐回应:“斋呀,斋呀!利呀!利呀!”(好啊!好啊!对啊!对啊!)领着我们二人朝山上爬去。到底是生活在山林中的人,爬起山来也健步如飞,我和伍解放自然不甘落后,使出浑身解数,勉强还能跟上。

到山顶时,他们四人终于停下来,围着几棵树转来转去,最后选择了处于中间位置的、双手可以和抱过来的那一棵树,他们一会儿用手指天,一会儿又用手指地,嘴里还不停的说者什么,苦于不懂傣语,只能一脸茫然看着他们,其中一位年龄较大一点的很吃力的说着汉语,双手还不停的比划,我们看着他的手势,很吃力的听着他说的“汉语”,多少理解了他的意思:这里有五棵差不多大小的树,中间这棵更高一点,以中间这棵为中心,可以看到外面,而外面看不到里面,搭建观察哨棚很合适。我和伍解放也围着这几棵树转了转,觉得他们的选择是对的,一边点头表示同意,一边竖起大拇指,表示他们是好样的。四个人很高兴,凑在一起商量。接着,年纪稍大一点的留下来,另外三个则离开了,我和伍解放比划着手势问留下来的那一位,意思是我们做什么?他摆摆手,然后又做出坐下来的姿势,看着我们笑笑。那意思是叫我们不用管,坐下来休息就可以了。我们自然不会什么都不做,但目前又能做什么呢?

只见留下来的这位又在中间那棵树上的两边用刀砍出一条条横沟,间距相等,最下边的那条距离地面大概有1米多,第二条沟与第一条间距40来公分,砍完第三条就停下来了,因为手已够不到砍第四条横沟的高度。他跟我们打了声招呼,也离开了。我问伍解放几点了,回答说:九点半了。过了将近一个小时,四个人都拖着一捆捆锄头把粗的竹子回来了,丢下竹子,四个又走了,来回三四趟,地上摆放着十多捆竹子,接下来一个削竹篾,两个拿着竹子在树上比划长短后,将竹子砍成长短相同的竹节,另一个将剖出来的竹篾刮得光滑一些,估计差不多了,两个开始在树上有横痕的地方,用长的竹节固定,再用短的捆在长的竹节两头,年纪大的那位站上去继续砍横沟,就这样一台一台往上升,捆扎了五十多台,也就是二十多米,已接近树冠了。

树林里越来越闷热,伍解放看看表,已经十二点快到下午一点了,难怪肚子“咕咕”地抗议了,正想埋怨几句时,不远处传来杜班长:“开饭了,开饭了”的喊声,我正要招呼他们四位下来用餐,却见他们坐在树杈上,从腰间的布袋中拿出一个芭蕉叶包裹着的东西,打开后直接用手捏着吃,原来是糯米团和一些烧烤过得食品,任凭我们怎么叫也不下来,只是笑着摆手。无法,我们和杜班长及炊事员在树底下用餐。吃完饭,杜班长从兜里掏出一包两头都能点火、只有连级干部才能享用的《金沙江》香烟,用垂下来吊竹子用的藤条扎紧,示意他们拉上去,见到香烟,他们没有拒绝,一边笑一边“利利呀!利利呀!”(好好呀!好好呀!),点着烟接着干起活来。

这五棵树的粗细高度相差不大,但分布就不那么规则了,毕竟不是人工种植的,相互间隔宽窄不一。不过,组成树冠的树枝却互相穿插,纵横交错,这为搭建踩板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用藤条捆住腰杆放到地面,比从上面一台一台地倒退下来省时的多,一人在下面用藤条捆住成捆的竹子的一头,上面的人将它拉上去,用扎篾把竹子捆扎在纵横交错的树枝上,围着中间这棵树的踩板就扎成了,踩板上靠树的两侧留有口子,供人上下。再在踩板的四周用竹杆横竖扎几道,又将有树叶的树枝扎在横着的竹杆上,有树叶的细树枝就铺在踩板上。原先在下面捆绑竹子往上递的那位青年人不知何时弄来两捆艾蒿,一捆铺在踩板上,一捆分扎在围栏四周,树上观察哨棚就大功告成了。树上三位下来时,将已剖成两半的短竹节扎在台阶上加宽台面成了上下的梯子,踩上去还比较结实。地面往上大概两米处的那几台台阶没有加宽,问他们,只是笑笑摆摆手,后来才知道是防备豹子之类的动物的。

交谈在费力中进行,得和年纪稍大的那位名叫岩依波,大概跟民兵队长岩依坎是同辈人,不知傣族是不是以字来排辈的,他要我们去看看是不是满意。我和伍解放踩着梯台往上攀,没费多大劲就到达踩台口,往下一看,心里有点虚,头有点轻微的眩晕,见他们四人站在树梯旁边,大概是担心吧。我们各从一边踩台口进到观察哨棚,见搭建得很是宽敞,四五个人值守,也不会觉得拥挤。哨棚四个角都用剖开的竹节并排成三角形捆扎在竹杆上,绝对是供坐下来休息用的。站立时间久了会有不适,坐下来调节以利恢复,想法很周到。哨棚四周栏杆仅高八十来公分,既可双手扶拦,操弄枪械,又保持视野开阔,四面环视不受遮掩,可见用心之至。从哨棚下来,连比带划,将四人夸奖了一番,并邀他们共进晚餐,他们却连连摇头挥手告别,从另一条路去了。

待我们回到“公房”,夜幕已悄然降临,吃完晚饭,向邓副营长报告了树上观察哨棚搭建情况,邓副营长听后也觉得满意,并告诉我们,今晚放心睡觉,公社“人武部”来人组织民兵夜训,会处理突发事件。明天早八点到晚八点,我和伍解放值守;晚八时到后天早上八时,由刘科长和江副排长值守,后天八时到晚八时,由雷科长和尹科长值守,后天晚八点到大后天早八时,我和伍解放值守,以此类推,直到任务完成,大家都没有意见,便早早入睡了。

吃完早餐,我和伍解放背着“半自动”,带上炊事班准备的午饭以及饮用水(军用水壶)来到拿巴山顶,攀着梯子进了哨棚,本想一饱眼福好好欣赏风景,但遗憾的是雾太浓了,浓得可以捧在手中,扒开树枝看向天空和四周全都是浓浓的雾。百无聊奈,干脆坐在角落的竹凳上——岩依波他们的设计倒真的派上了用场。闲的无聊,不如擦拭“半自动”,我退出子弹,卸掉枪机,掏出手巾准备擦拭枪管时,发现枪身一尘不染,乌光净亮——雷松柏这鬼儿子真是太负责了。叹了一口气,重新装上枪机和子弹,把枪靠在一边,和伍解放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起来:伍解放也是跟随父母来云南支援边疆建设的,比我大两岁,农场军管后成立机务排,他被调进开拖拉机。人很老实,也肯出力,跟师傅数载,除了擦洗,打黄油,磨汽门,就是给师傅们清洗工作服,吃苦耐劳,很得师傅们赏识,终于让他单独出车执行任务,营里成立执勤小分队,他被命令为队员之一(不是选拔而是直接下命令),这次又被点名参加观察哨行动,可见营部很是器重他。可惜,文化程度只有小学,不然前程不可估量。聊着聊着,我发现雾没了,太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哨棚里,那一道道光柱好像是金黄金黄的,难怪人们会说“金色的阳光”,还不大相信,现在真是大开眼界了。我不由得扒开树冠上的一根小树枝,放眼望去竟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天,湛蓝湛蓝,没有一丝云彩,苍穹之下,白茫茫一片,风像一位慈祥老人的手,爱抚地拂动着无边无际的白色波浪,波浪涌动着,翻滚着,时而托起绿色小岛似的群峰之顶,时而像涌动的巨浪又将小岛吞噬,阳光像魔术师给涌起的巨浪,飞溅的浪花,翻滚的浪涛抹上了一条条不规则的金边;这绿色的峰顶又像一艘艘没有桅杆,没有风帆的摇摇晃晃的船,时而被浪花淹没,时而被巨浪托起,时而被波涛推移,波涛下方似乎有一个巨大的洞,涌动的浪花渐渐的平息,渐渐地褪去,峰峦像穿上了翡翠般的绿彩裙,晃动着发簪羞涩地笑迎着太阳。远处,一幅镶着金边的白云腾空而起,渐渐地幻化出稚童般的笑脸,挥动着胖胖的双臂,似在告别大地,或者似在告诉大地,明晨,将重新与五彩的大地深沉地偎依。“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此时的重峦叠嶂,确是五彩斑斓;木棉、梨花、李花、杏黄、紫荆……树叶:嫩绿,嫩黄,绿,深绿,蓝,深蓝……一眼望去,就是硕大无朋的五彩斑斓的地毯;刚才,浓雾翻腾的雾山雾海,绵延无际的五彩画毯,都使人产生强烈的欲望,到雾海中畅游,到彩毯上嬉戏,大自然造化无穷,大自然变化无穷,迷人的野景,真热剪载一幅或作窗花,或置床头,定格时光,储存思忆,富美生活……群山,才刚苏醒似的,山风轻快地掠过树梢,带走树叶欢快的“沙沙”声,树冠也受了感染,也笑着前仰后合,此时那橙色的巨幅画毯却似波浪一般此起彼伏,“山风吹,林涛吼,好一派南国风光”。山风推动了林涛,林涛惊动了“精灵”,画眉、鹧鸪、布谷、百灵、斑鸠,还有穿着燕尾服的绅士……一边欢叫着,一边乱箭穿云,酣畅淋漓地上演着歌舞秀(其实是在捕食藏不住的小飞虫),我痴迷了,直到伍解放在我耳边说:“该吃午饭了”,我这才回到神来。

版纳的三月,下午阳光炽热,知了永远不知谦虚,什么都是“知了”(拖长了声音),鸟儿们似乎也闹腾够了,敛着双翅躲在树叶下假寐;没有一丝风,树很安静,只有那不知疲倦的“知了”还在振动着翅羽,重复着烦人的声音……“金乌”西坠,山林开始躁动。一整天,没见什么异动,刘科长和江副排长来接班了。

上树冠观察哨的第二天晚,我和伍解放值夜,除了蟋蟀弹琴,夜鸮凄厉哀啸和不知名的鸟的“夺夺”声外,时而还有一种幽怨沉长的声音,原始森林的夜,既神秘又恐怖,光是前面的那几种叫声,就足以让人汗毛直立,不寒而栗。我和伍解放分工,每人值2小时,轮换着坐或睡2小时,养精蓄锐,一夜无事。

第二次晚上上观察哨棚,是三月十三日,也就是分组值守的第五天夜晚,听不到异常响动,僻如夜鸟惊飞,野兽惊跑,看不到火光等等,我和伍解放商量;晚上值守就由我们包下来吧,我们毕竟年轻,耐得住,他们白天轮值就行了,伍解放同意。我们将想法告诉了邓副营长,邓副营长思考了一会儿,也点头同意,叮嘱我们:不到万不得已,一定不能鸣枪。

第五次值夜是三月十六日,月亮比平时明亮,光线从树枝缝隙中透入,尚能看清地面的情况,子夜即十四日凌晨1-2点时段,是我巡视,伍解放大概睡着了。这时,“唏唏嗦嗦”的声音从地面传来,我顺着声音往地面搜寻,见一小黄牛般大的野兽正向我们所在的方向走来身体碰擦矮小的灌木,发出“唏唏嗦嗦”的声音,时而停下来抬头仰望,不一会儿来到哨棚下面。我赶紧推醒伍解放,轻声在他身边说下面有野兽,伍解放起身握着枪轻手轻脚地来到围栏,我俩朝下看去,见它在围着树转圈,月光时不时照在它身上,花纹也时隐时现,我俩屏住呼吸,分别蹑手蹑脚挨近踩台入口,枪口指向还在绕圈的野兽。过了一会儿,那野兽贴着树干,两只前爪用力,抓划树干,听得见树被抓破的声音,但感觉不到摇晃,因为哨棚踩板和围栏已将五棵树连在一起。好一会儿,那野兽前爪落地,在树的根部刨了一会儿,又将身子立起来,只听见轻微的“淅沥,淅沥”声传来,那野兽又绕着树干转了几圈,便干脆靠着树杆躺了下来,我总觉得它身上的花纹极像是老虎,约摸10多分钟后,它站起来抖动身子,抬起头来望望,慢慢腾腾地钻进了灌木丛,随着“唏唏嗦嗦”的声音渐渐远去,我们俩从踩台口收回枪支,不禁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早上,我俩向来换班的雷、尹两位说起此事,二人起初还满脸狐疑,待见到树干上的抓痕,树杆周围地上的爪印,地上的泥坑和树上的腥臊味,方才相信。

回去用完早餐,已是九点半,倒头便睡,醒时已是下午二点,觉得很热,便叫上伍解放一起去那个浅潭洗澡(因为拿巴河的水是从深山中流来,较冷,怕洗了生病)。说是浅潭是相对拿巴河而言,其实一下去水也到了胸部,擦洗了一会儿,准备上岸,只听见倒在水中的枯树那里传来:“哗啦”的响声,我和伍解放涉水到枯树边,见枯树露出水面部分有个大洞,里面是空的,水中有很多露出脊背的,很像是鱼的东西紧紧地排列在一起,我大着胆子将右手伸进去捞出一条,真的是鱼,奇怪的是这鱼是扁形的,比两个手指头宽一点,侧面比巴掌大一点,眼球浑浊无光,除鱼背带浅黑色外,通体灰白,鱼鳞细薄无光泽,手握着也不会动一下。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抓上来再说。等我俩把大的抓完,地上大概有五六十条吧。伍解放跑回炊事班叫来杜班长,杜班长一看,摇摇头:这鱼刺多肉少,很费油,拿几条今晚上吃,其余的剖开,没有盐,晒干吧。伍解放脚快,又跑回去拿了几个盆和筐来,三人一起剖鱼,除了老杜拿去10条,还有六十条,干脆摆在枯树上晒鱼干。

晚上十点刚过,就来了客人——大大小小十来只野猪,这从“哼哼叽叽”的声音可以判断出来,伍解放借着树叶缝隙下来的月光,将枪瞄准靠近树身的那头大的,我轻声对他说:不能打,老人说:“打老虎靠胆,打野猪备板”,那意思很明显,打老虎要靠胆量,打野猪要准备好棺材。况且,你即便打死了一头,其它的会立即展开报复,它们的牙齿对于这样的树来说,树可是扛不住的,伍解放无奈的收回了枪,想起邓副营长叮嘱的,只能摇摇头作罢。那一群野猪大概是闻到了老虎的尿味,在树根部拱出好大的一个坑,就“哼哼叽叽,哼哼叽叽”地离开了。

第八次值夜是在三月十九号,我想,几天来,不见有异常情况,昨晚“客人”也没来,今晚也不会有什么情况吧,就靠在围栏边透过叶缝数天上的星星,直到伍解放来换班。午夜两点,我打着哈欠来到围栏边,月亮才升上天空,脸庞白黄白黄的,光亮还不如夜空的星星。我问伍解放,头灯带来没有?他将头灯拿给我就去睡。我将头灯戴在头上,以备不时之需。睡意来袭,哈欠不断,我只好顺着围栏来回走动,时不时看看伍解放的手表。这时间实在过的太慢了。在四点还差十分的时候,一道昏黑的影子在朦胧的月色下,慢慢地向哨棚走来,我还以为是眼睛花了,揉了揉眼睛,确实是向这儿走来的。那黑影越来越近,我等它接近树杆时,突然打开头灯,光柱照在它的侧西,竟然是一头长着角的马鹿,那角很漂亮,宽大又有好几个分叉,这是一头老马鹿。令我惊奇的还不是那鹿角好看,而是这头鹿见着灯光并不惊慌,反而,抬起头来迎着灯光“昂”地叫了几声,那眼睛的反光是绿色的,见没有回音,才低下头嗅着什么,可能是老虎的尿味还没有散尽,只见那马鹿开始显得不安,加快脚步隐没在灌木丛里。我抬起头,望向它消失的方向,再也见不到它的踪影了。后来我问邓副营长何故?邓副营长说,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你的头灯灯光是淡绿色,它有可能认为是同类。第二种可能是它处于求偶期,反映有些迟钝,后来闻着气味不就很快走了么。我想想有些道理。

第二天下午,也就是三月二十号下午,我和伍解放收拾完鱼干回到“公房”,见同事彭代浅正和邓副营长说些什么,我想可能又有什么任务了。邓副营长见我们回来,就说,晚上不用去值夜了。开会,宣布团部命令。

团部的命令就是:美国的飞行员已经在水利五团辖区落网,搜索任务结束;营部要我们撤回。

与队长岩包依,民兵队长岩依坎,岩依波他们四人和几个“老波涛”告别,我们便离开了曼巴拿寨。下坡路有时也不好走,刹不住脚,走了大概两公里多路,原来阴沉的天下起了雨,都没有带雨具,只好脱下外衣顶在头部。别人还好,倒霉的是我和伍解放,那些用藤条捆绑的鱼干被雨水浸泡越来越沉,路越来越滑,那些鱼一会儿甩向左,一会儿甩向右,弄的非常狼狈。杜班长看我们狼狈的样子就说:丢了吧,弄得到处鱼腥味。说完,走到我俩身边,用刀子割断藤条,将鱼丢了一地,我们摇摇头,一笑置之。

搜索任务结束,历时十五天。所谓搜索跳伞的美蒋飞行员,其实是高科技的无人侦察机,“抛弃副油箱”的说法,一是政治斗争需要,二是为了隐蔽地进行搜索行动,便于逆向工程科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