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屋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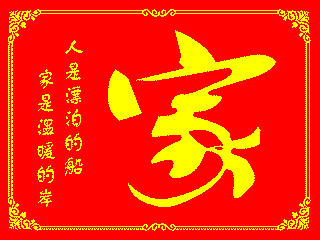
我说的老屋就是老家的屋。有人说:"有过你的东西的地方,就是你的家!",心也好,屋也好,身体也好,灵魂也好……只要有存放的地方,就是你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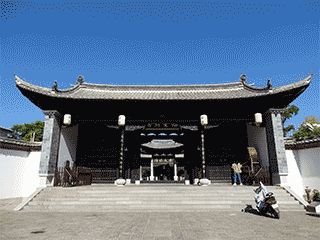
我最初记忆的阳光,是在县政府的一栋老屋,青砖碧瓦,我时常在屋内的床上蹦跳,手拉一具彩色的玩具手风琴,咿咿呀呀的乱唱一堆谁也听不懂的歌,等着一缕阳光从门外射进来。这时,我和妹妹就会得到一碗热腾腾的面条,我还特爱吃那种,半生的面条。

县政府的朱门时常关闭,但门下还有缝隙,阳光会从门外透进来,我也会时常钻出去,手里捏着两毛钱去县政府外的紫林寺打新鲜牛奶,又从门缝钻进来,递进500ml的牛奶。那朱门太高了,上面还不满了圆形的大铜钉,铮亮铮亮的,我不觉得好看,倒觉得很恐怖……

县政府内住的人不多,有许多苍天的大树,还有许多高耸入云的桉树,会掉下树皮还有长长的枝条和落叶。我们就捡拾这些枝叶,来煮牛奶。

县政府内有一口大井,奶娘常背着我去挑水。每次她低头打水时,我都被吓得鬼叫,像是要掉进井里。井是绞车井,有一次奶娘打水竟绞出一条水蛇,杨娘吓得把桶一丢,就往后跑。水蛇还缠在绞绳子上,这是我第一次记得的最恐怖的事……

在县委大院时,还有一事,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缺乏食物,奶娘的儿子小红鱼就去摘蓖麻籽来给我们吃,我们没有吃,他自己吃了,结果中毒了……抢救及时,救回一命……

3-4岁时,父母调离县政府,我们的家也搬离了,在陈官镇棕绳社后面的一个青砖碧瓦的小院内居住。这也是个老屋,不知是哪个地主的财产?反正院子很大,还有后园,有一次我在后园见着一条盘着的纯白色的小蛇,叫来奶娘,蛇却跑了。父亲在西庄任区长,母亲在陈官任书记,我常不能见到父母,而跟奶娘杨娘睡!那老屋有里外两间,里间较大是父母的卧室,外间是我与奶娘的睡房,屋外有一石铺的天井,天井内有石桌,阳光下的院落,是我认字的地方,父母教认字,很独特,举一反三,总是教一得三!

人-从-众;木-林-森;日 – 昌 – 晶;就这样,我3岁前,竟然认识了几百个字(后来教儿子英语,也成了class-lass-ass-as)。父亲在西庄乡会桥的区公所有一间屋,有一尚明亮的玻璃窗,阳光会照进来,麻雀总是朝窗飞。于是,当阳光从窗透入时,父亲就打开门,让群雀飞进去,关门捉雀……每天能捉20多只,开膛破肚,用盐腌制后,风干,油炸……那肉的滋味,绝对鲜美,为逮雀,早已顾不得他们的挣扎与哀鸣……3年困难时期,"对三月不知肉味和水味"的人来说,鸟就是不要钱的肉味和美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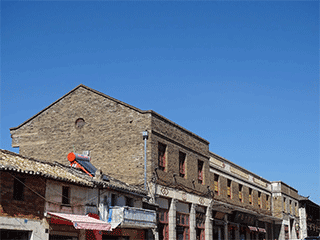
我们又搬家了,母亲调任饮服公司做经理。我们搬到了东正路, 一家青砖碧瓦的四合院,那是建水饮服公司的公司地址(大约是1966年前后)。我家搬在这里,住在底楼。二门外水井旁,有一间房屋,既是厨房,又是卧室,这是全家的客厅,地板是土夯成的,最有记忆的就是光线, 阳光从屋顶清灰的瓦缝和亮瓦中泄露下来,光线穿过灰暗的空间,照射在蒙尘的木窗户上,粉尘,飞扬在透亮的光线里,轻歌曼舞着,投射在地上的斑影很是好看,杂物上的光纤,也随着光缓慢的移动着,这种旧物的光芒,在任何时候,都让我感到持续的亲切。屋旁有一口水井,井旁立一木柱,柱上绑着竹竿,竹竿的一端系着水桶,另一端系有石块。打水时,只听桶,噗噜噜,水就被竹竿提上来了。我们在这里玩水。在井边过家家,墙角踩花煤,四门市剥豆,抢读报刊,恶作剧,偷食糕点,就发生在这一时间……

公司里的有个叫普济奉的叔叔,对我们全家很好,这个叔叔能歌善舞,教我们唱京剧《沙家浜》,老五唱的最好,脖子上的大阳筋都露出来了……“适才呀!听得司令讲:阿庆嫂……”,后来这个叔叔不幸病逝了,很遗憾。

在这时间段,我们偶尔的早点,就是周末的豆浆,油条和米线,父亲找来一只5升左右油漆桶,周日去盛豆浆或米线给全家吃。油漆味的米线豆浆,我们吃着生长着。童年的快乐就是玩,玩过家家和"打死救活"——一路疯跑,你追我赶。

文革导致物资匮乏,买什么都要凭票,所以我们家有了许多的票,米票、肉票、火柴票、布票、酒票、肥皂票、烟酒票……票剩着,好些时候是买不起。我和二妹一遍又一遍的围着百货公司乱逛,空瞪着眼睛望着玻璃柜的里的东西动心思,说我想要这样,我想要那样,等我有钱了,我想要这样……管他什么东西,都空着去数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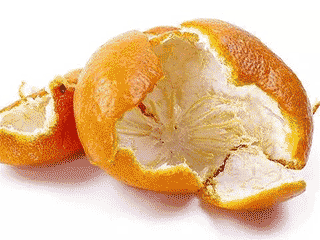
满大街去捡拾人丢掉的橘子皮,石榴皮,桃子核……洗净晒干去药材公司卖钱……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去四门市做童工,领着弟妹们去抢豆剥,剥一斤蚕豆,得2分钱。剥一斤豌豆,得1分钱。周日就是这样度过!再长大一点,就去四门市收碗洗碗,一天的工作超过12小时,得1块3分钱。这1块3分钱,是含着血水和汗水的,12小时内,脚不能停,叫:“跑千里路不出门”,累到死。

不知何故,我家又搬家了,搬到马市街的沐浴室,确切的说,是搬进一个庙堂,洗马潭边的庙,说叫"接待寺"。父母住正殿,我和妹妹住偏殿,有一小天井,外婆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没有水井,洗衣就去洗马潭。煮饭的水,要去1-2公里外的紫房巷去挑,紫房巷的水是甘甜的,和西门水一样。煤,买煤凭票,还要到几公里外的火车站去抢,捡到拳头大小的那是上好的煤。一挑,就是50斤。在这里,老五6岁就学会了生火煮饭,那木蒸子,还是用头顶进锅里的,顶着星星,排队去买蚕豆豆腐,7分钱一斤,一周只卖一次,很难买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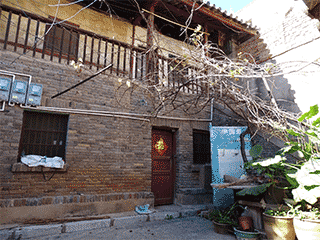
吃菌子,全家中毒。外婆摔断腿,发生在这段时光,1970-1976年,我家搬到了马市街饮服公司食堂住,一住就是几十年。现老屋还在,父亲在老屋内度过了他的最后时光,父亲的几十年,都以幸福和痛苦的方式,铺成在那些旧物的时光里,一张大床,一只衣柜,一组自制的木沙发,护城河里"捉鱼",挖野菜,拾柴火,填鸭子,养大花狗,栽葡萄,上山下乡,工作……就发生在这段时间里。

院内有一口水井,伸手就可以打到水,厨房里,父亲总会变戏法的弄出许多美食……

我一直说不清楚,这些年一次一次的离开家乡,在远远的另一端奔跑,是对本真世界的远离?还是靠近?我到底在旧屋中寻找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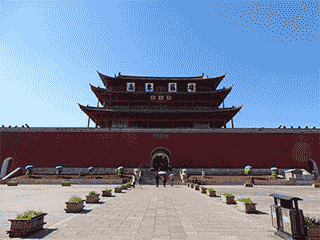
知天命年,我才清晰,对建水老家的热情,其实是一种精确的缅怀和依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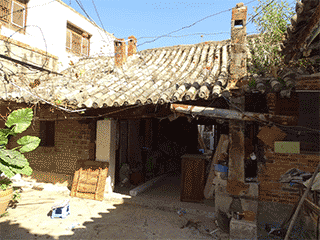
我们曾经远离的老家,是给予我丰富营养的地方,曾经的苦难那是通往幸福的基石。

我们远离故土,告别伴随我们成长的老屋和田野,到一个遥远而浮躁的地方寻找人生,苦苦挣扎在名利,虚荣,金钱的喧嚣中……像一棵不再生长的树,萎缩在虫蛀的历史中,想念着土地和阳光的恩情。当所有的意义和目标开始花白以后才明白。能够还原生命的,依然还是远方的故土,以及老屋里那些废弃或即将消失的旧物。

老屋的旧物,是剩余在生命中的温暖,尽管它可能已经残败,废弃,和面临拆除。但他们留存的时光,总以安静的手势,抚慰着我们想念故土的心灵。

我们有过苦难,家庭的,我们永远想象不出,我们的父母亲,及祖辈们经历过什么样的艰辛和痛苦,让我们七姊妹一个不落的活下来。

经历过文革和上山下乡,整个童年围绕着生存的苦涩记忆,就深刻留存在那些成年的旧物上,门背后,墙角落,落满尘埃的蜘蛛网——止血剂;老墙上的竹篮和绳套——挑煤炭。屋檐下堆积的柴火——铁路上捡的桉树枝。

我们的童年在老屋里,恩情也在老屋里,我们的童年,是苦难和幸福的童年,恩情是故土和父母的恩情。

儿时经历的艰难伤痛,也是一种财富,正因为有儿时的苦难,才有我们背井离乡,奋发图强。也因为故土的滋养,和父母的恩育,才成就了我们的事业。

有很多时候,都希望有一种时光,让我们坐在暖暖的阳光中,安静的靠近老屋,沉缅于旧物的光芒,一次次看着时光在旧物上闪亮,移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