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色幽默

鼠年来了,总觉得这个老鼠不那么可爱。但是为了过一个别样的鼠年,我早早的就买好了1月14日的火车票,临近上车了,遭遇的是北京寒冷的冬,所有的人都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口罩耳罩,各色风衣,组成了另类风景。我,拎着一袋速食快餐,匆忙的登上了开往昆明的列车,上了顶层卧铺,睡不着,总是莫名的空落。拿起手机,看到了“楚国”的不快信息,SARS的变种,新型冠状病毒在吞噬武汉,想着有个妹妹弟弟在武汉读书,总是觉得有些担心,也不知他们放假是否已经回到南方?

两夜两天的火车,我就靠着这些速食度过难熬的30多小时,第三日中午,安抵昆明。昆明也像北京一样的见不到蓝天,总是觉得很压抑。我立即买了到建水的动车票,两个小时后,奔回了自己的衣胞地——建水。那是我断脐的地方,我有着浓厚的感情。见了外婆,看见外婆摔坏了手,手青肿着,心情更沉重。外婆毕竟是接近90岁的人了。告别了外婆,又赶紧爬上了去景洪的客车,10个小时的颠簸,到达黎明之城——景洪。好在我在景洪有个蜗居,沉沉的睡了一觉,第二天,又孤零零的背着我的黑色大包前往勐海,勐海——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打开电脑一看,知道冠状黑色病毒在全国蔓延开来,病毒的发源地武汉开始封城。“唉,我也曾坐着列车穿越过湖北,还是汉口停留过几分钟”。庆幸冲出了“楚地”,来到温暖的南方,过一个鼠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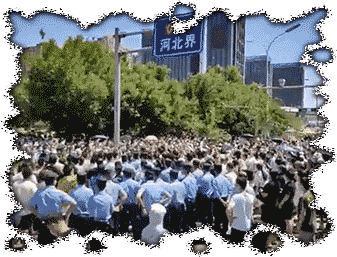
危机!危机!危机!我驻足过的北京、燕郊、昆明、建水、景洪统统都发现了来自“楚国”的病毒,中国已“四面楚歌”。封路,封城,一日比一日严重,先是北京的住宅小区追问电话,问我在哪里?我说在云南,他们就说别回来了,我们已封小区。后是勐海派出所、防疫办、父母的单位统统都来讯问我这个“不速之客”,连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勐遮派出所一天之内竟然来了两个电话,说电脑显示我去过勐遮。其实,我只是和勐遮的一个发小在城里小聚一下,根本没有去过勐遮。
今日在朋友圈看见一份政府签发的行政令,勐海宣告“全面封城”。凡7号0点进入勐海的人(包含勐海籍),一律到指定地点集中医学观察14天……这是一场知道结果,却不知过程的马拉松。不知是谁开启了潘多拉的魔盒,让全国告急,中国成为孤岛,外国彻底中断了来华的航班。我是难回北京了。心焦气躁,恨不得在地上跺它几脚。沉重的房贷,因封城的“失业”,缺钱,没钱,心情十分难过。庆幸的是,我的囚笼在市郊,半亩家园,2条狗,4只猫,5只鸽子,18只鸡陪伴着我。夜半,我登上屋顶的大晾台,遥望满城灯火,想着那些关在火柴盒房子的人,比我更惨。中华文明5000年,这是五千年来最严峻的封城,我忽然听到一哩哇啦的大喇叭响了,说些我听不懂的傣语,但我猜大概是在说封村的事。
这些天,看见了各种各样的资讯,都是各种方言组成封村的表演;有戴红袖标手持红缨枪的;有装关公耍大刀的;有村长敲锣叫封村;有人在家里发癫疯唱;最可怜的是从西伯利亚飞来昆明过冬的海鸥,无人投食,一群群的坐在马路上,等着政府救济;还有一只猫,在空无一人的广场上,跳着大妈们常跳的广场舞……黑色的幽默。
这场人与生物的战争,拷问我们的灵魂,除了悲叹,我们黔驴技穷。物资短缺,物价飞涨,在百元一斤的鲜肉摊前望肉兴叹,在60一棵的大白菜前,苦笑稀稀。和平环境惯坏了我们,我们无法应对突发的灾难。
街上没有行人,没有人理我们,安静的可怕。我只有领着我的两条孤零零的狗,去寂静的田坝里溜达,田坝里荒草萋萋,没有庄稼,没有绿色。走近尨山,见密匝匝的森林,恐怖诡异,那是傣族不敢走近的地方,他们认为那里有神灵。在这无人区,我却看见一只野鸡,张开翅膀,拖着长长尾翼,在空中盘旋,特别的漂亮和耀眼。还看见几只鸥鹭,在草丛中做窝。唉,它们是那样的自由。我呢?只能扼守这几百平方的家园,浇浇花,搬砖砌花台,在田野中捡牛粪,做堆肥。哎呀,也不知空气中会否悬浮什么东西,出门就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像极了古代的绿林好汉,却不知在哪里剪径觅食……
在勐海,曾经见了儿时的挚友,一个公务员,一个是创业老板,各自都有一肚子的苦水,大家为了生存,趟深水,过火海,方向很迷茫,现实很残酷。
管控!管控!天空管控,交通管控,车辆管控,人员管控,封巷,封城,封村。打开手机,打开电视,出现的是一段段的方言,一段段的口号,一条条的标语,空街,空巷,一幅幅的画面,心中五味杂陈,我想起了毛主席的诗词,千村霹雳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人祸天祸,华佗无奈小虫何?
我终于看到了没有硝烟的战争,人类与生物的拉锯战。像极了美国的科幻片《末日孤舰》。
唉,黑色的陷阱,黑色的灾难,我只能在黑色中幽默,苦笑……